一部恢弘的草原英雄大传
一首唱给中亚大地的赞美诗
一段草原儿女爱恨交织的悲情故事

图书简介
著名作家高建群的最新长篇小说《中亚往事》,是作者根据自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从军经历和多次丝绸之路文化考察见闻,书写的一部兼具传奇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草原英雄大传。讲述了主人公马镰刀由骆驼客,到“草原王”,再到北湾卡伦站长的身份转变和曲折跌宕的悲情故事。
小说中既有自然景致的细致呈现,又有人文历史的独到挖掘,将中亚的辽阔、丝路的壮美刻画得淋漓尽致。该书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教育部2023年主题出版重点项目,陕西省2024年度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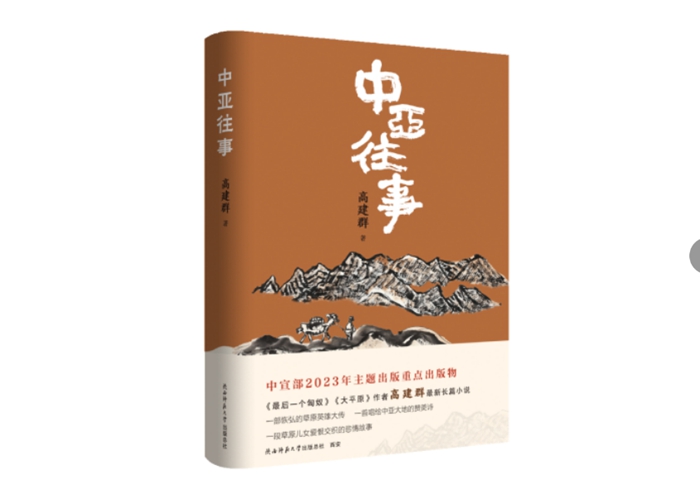
《三班长的后白房子故事》
选自《中亚往事》第479—500页
两千多年前的中亚地面,像一口翻滚的大铁锅一样,游牧民族的马蹄,风一样地来去无定。人们把这个时代叫作中亚古族大漂移年代。而阿尔泰山山脉、额尔齐斯河河谷地面,则像一个大狩猎场。
舞台已经搭好,幕布徐徐拉开,人类该登场了。人类是依次登场的。原谅我们的笔墨,不能将那些依次登场的演员一一点到,我们只能择其大要、略表一二而已。
01
我是在200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抵达白房子的。汽车顺着喀拉苏干沟时断时续的水流,穿过稀疏的林带,自北向南,一路走去。这段路程是二十公里。记得我以前说过,我曾经许多次骑马走过这条道路。
晚上9点,用乌鲁木齐时间来说,才仅仅7点,但是天已经完全地黑了,暮色四合,天地暗淡无光。戈壁滩、树林子都一片朦胧,宛若梦境。天不应当黑得这么早的,因此我怀疑这是我的错觉。
现在正是盛夏,正是这块地域有北极光的季节。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这个季节,太阳虽然早早就沉落得没有踪影了,但是从太阳落下的西地平线上,会有一道强烈的白光射出来。白光射到天上,散开来,落到戈壁滩上,于是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种柔和的、奇异的白光中。
我记得,我抱着枪站在碉堡前面,跟前的芨芨草滩白光闪闪,一只硕大的母刺猬领着一群小刺猬,从我的脚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1974年3月 摄于新疆白房子
我用枪刺轻轻地一挑,挑起了一个小刺猬。所有的刺猬听到响动,闭合了,蜷作一团,像一个个带刺的皮球。我将那只最小的刺猬,用手试探着抓起,包进手帕里,再将手帕扎紧。手帕扎紧后,刺猬猛地一下张开,于是硬刺从手帕扎出来,扎得我手上鲜血直流。我赶紧把它扔到地上。
相较于我当兵的那个年代,白房子的地形地貌,已经变化得叫我难以辨认了。记得那时,灰蒙蒙的戈壁滩上,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白房子的顶上,有一根烟囱。一日三次,那烟囱向天空升起直直的、细细的炊烟。那情形正如浪漫曲唱到的那样:卡伦一日三次,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早安,午安,晚安。
一圈矮矮的、厚厚的黑色碱土围墙,将这白房子围起。圈子里有个篮球场,有个马号,有战士厕所和干部厕所。黑色碱土围墙也起着掩体的作用,上面布满了方形的射击孔。
院子里栽着一些树木。篮球场被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围起来,这冬青冬天会被人用积雪拍成一堵雪墙。此外还有杨树、榆树和沙枣树。最奇异的要数那棵野苹果树了。那时我在一班,这树在一班住房的右手边,也就是说,是在院子的西北角。
大门里边,则有一个中世纪的吊杆,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吱吱呀呀地从井里汲水。井在正北方向,大门的右侧。那时的道路,在正北方向,面对阿尔泰山。记得,大门外面有几个突出的沙包子,兵团的那个腼腆的邮差小伙子,站在沙包子上,勒住马、吆喝着叫挡狗,说“你们的家人来信了,快来领信”。
那时的瞭望台,在靠近界河的地方。瞭望台距离白房子大约有五百米远。它是木质的,高三十米左右,通体发黑,肩一天风霜,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遇到刮大风的时候,瞭望台会像一个醉汉一样,在空中摇晃。迎风一面的牵引钢丝,绷得笔直笔直,背风一面的牵引钢丝,则软蔫蔫地弯成弧形。
记得,有一次我上瞭望台的时候,皮大衣被大风剥掉了。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人没有被刮下来,而大衣被剥去了。我唯一能为此事做出的解释是,当我换攀着扶手的这只手时,风脱去了这只袖子,我换另一只手时,风又脱去了另一只袖子。
现在的白房子,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02
瞭望塔上,正当我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时,突然被马儿的一阵尖叫声惊醒。这是伊犁马的叫声。一匹马先叫,别的马应声附和,于是马儿愉快的尖叫声,像多声部的花腔女高音一样,打破了这荒原早晨的宁静。这是边防站的马。
那个年轻的蒙古族小战士,正把马从马号里赶出,往比利斯河方向去放牧。马号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现在的马号,在土围子外边的东北方向,紧依着喀拉苏干沟。那地方原来是牧工的毡房。
在我的白房子传奇中,那里是叶丽亚居住的地方。
记得我曾经说过,我来到白房子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看一看我那匹额上有一点白的坐骑还在不在,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看一看我当年背过的那个6940火箭筒,现在是由谁在背着。
马一旦放出去,得晚上才能赶回来。于是我赶紧下了瞭望塔,赶往马号。我对那位面色黝黑的蒙古族小战士说:“给我抓一匹马来骑!”“你要骑马到哪儿去呢,老班长?”小战士说。我说信马由缰,骑到哪儿算哪儿。小战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马群重新赶到马号。一群剽悍的伊犁马站在我的面前。马的屁股浑圆,脖子修长,屁股上打着号码,匹匹都是好马。
我寻找着,看哪一匹马的额上有一片白色。后来我失望了,因为所有的马的额头都和它的皮色一样,并没有一匹白额马。我不甘心。我比比画画地对这位小战士说:“有一匹马,鼠灰色,额上有一点白,像个骡子,走起路来一趔一趔的。那曾经是我的坐骑,它大约不在了吧?退役了吧?
小战士问我离开白房子多长时间了。“二十三年多一点!”我回答说。小战士笑起来,他说:“这马不知道都换过多少茬了,你比比人吧,一茬一茬的兵,走马灯一般,都换过多少茬了。”我也笑起来。我同意他的话。小战士抬起眼睛,望着空荡荡的远处说:“都这么多年了。那匹马我接手的时候就没有见过。它该早就退伍了吧。如果它还没有死的话,要是在城市里的话,它现在该在拉粪车,要是在乡里的话,它现在该在某一块田里拉犁。”
他说的是实话。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这位可爱的小战士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这个老兵罗曼蒂克的想象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小战士为我挑了一匹黑色的大走马。我坚持不要跑不快的驽马,我说骑上它是对我的昨日的一种不尊重;我也不敢要那些暴躁地砍着蹄子、扬鬃乍尾的烈马,我的身子已经十分臃肿了,我担心被它甩下来。这样,小战士为我挑了一匹聪明、利索,没有任何怪毛病走得又快的黑走马。我坚持要自己为马披上鞍子。
我走过去,马看见是个穿非军装的人,惊恐地一趔身子。我没有退缩,我像遇见了一个老朋友一样,将它的脊背先拍了几下,算是打招呼。尔后,又拍了几下它的脑袋。在拍脑袋的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在马的耳根轻轻地搔了一阵。在搔的过程中,马的身子不再颤抖了,它舒服地放了一个响屁。最后,我伸开双臂,紧紧地将马头抱进我的怀里,将脸颊贴在马额上。贴在马的脸颊上的时候,我双目潮湿。
很久很久以后,我的情绪才平复。我提起鞍子,使劲一甩,将它披在马的背上。尔后,按照当年副指导员所教给我的方法,伸出一只脚,从马肚子的另一面钩住马肚带,用手捉住,系紧。系完前肚带,又系后肚带。在系马肚带的时候,我想起副指导员常说的话:骑兵的命在马肚带上系着。这样,小战士给这匹黑走马安抚性地吃了一瓢豌豆草料以后,我便骑着它上路了。
03
午饭很丰盛。因为我们的到来,连里专门宰了一头猪。本来是要宰羊的,不过羊群转场到阿尔泰山深处的高山牧场去了。吃罢饭后,老杜临时提议,在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在边防站举行一次军民联欢会。
这是我在白房子看到的第三次慰问演出活动。
联欢在边防站的军人俱乐部进行,老杜的小女儿,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担任主持。老杜的大女儿则翩翩起舞,和边防站的维吾尔族排长跳了一曲维吾尔族舞蹈。随行的姑娘们,也都纷纷请战士跳舞。那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拽起满脸通红的连长,弄得连长狼狈不堪。
我坐在那里,浑身充满了一种幸福感。我傻乎乎地笑着,像那些脸上叠着许多蚊子咬的大包的大兵一样傻笑。我深深地感激兵团人,我相信,这些大兵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将长久地记住这个节目,将姑娘们的大眼睛和连衣裙谈论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该走了,该向我的白房子告别了。
我最后一眼望向那白房子。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和我当年第一次见到它时一模一样。
连长说,明年这房子就该拆了。那时边防站要起楼房。现在别的边防站已经盖成了楼房,北湾边防站是最后一个。
是的,白房子该消失了。正像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的归属已经不存争议了一样,这个一百年前的故事应当结束了。当然以后还会有新的故事,但是那已经不是从马镰刀开始的那个故事了。
白房子也应当从我的记忆深处消失,从而让这个老兵有一个平和的晚年。
全站列队,送我们走出大门。我搂着连长的肩膀,搂着指导员的肩膀,长久地搂着,不忍分开。我努力做到使自己不哭,结果我做到了。然后我飞也似的跑上汽车,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汽车开动了,我的白房子被远远地丢在了后边。我是在2000年8月29日午后3点离开白房子的。
正值中亚细亚阳光灿烂的中午,我们的汽车在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中行驶。阳光闪闪烁烁,在这金黄色的海洋上跳跃着,令人头晕目眩。“这是祖国的土地——无可争议的祖国的土地。”当我在这片金黄色的海洋上行走的时候,眼望窗外,我喃喃地对自己这样说。
现在由我来赞美,我的祖国的泥土吧!它曾经差点失去,现在又重新获得。哦,这是我们赖以立足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我们代代相袭的土地。

|
